《一顆頭顱的歷史》
前言
今日,對於每一個正在讀這篇文章的你我來說,「屍體」在這個社會中基本上是一個被隔絕的、極為罕見的「物體」;除了自己摯愛親友往生的葬禮上,我們絕少看到屍體,更別說是看到一顆與身體分離的頭顱了。也因此,對於那種與身體分離的頭顱,我們直覺地覺得可怕、覺得會去把人頭砍下來的人真野蠻。
之所以覺得可怕的原因不只一端。專門研究大腦的學者早已證明人類天生就能判讀其他同類的表情與肢體語言,而且早在我們「意識到」之前,我們就已經「察覺到」了;也因此,當我們面對一顆有血有肉、五官清晰卻少了軀幹四肢的頭顱,我們與生俱來的判讀本能當機了,於是你我感到莫名的恐怖。
總之,提到砍頭這件事,我們大概都有類似的既定印象:我們是文明人,而文明社會中很少見到「砍頭」這種事情,所以會幹這種事情的人,應該就是「不文明」了;又因為我們這麼少見到「砍頭」這種行為,所以總覺得那應該是存在於遙遠的過去、又或者是發生在蠻荒的原始文明。
「殘忍」、「古代」、「不文明」。誰最符合這樣的印象呢?嗯,應該就是原住民了吧!因為,刻板印象中,所謂的原住民直到近代還遵守著傳統的文明習俗,所以直接符合了「殘忍」、「古代」、「不文明」這三張標籤。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我們不能只把切斷的人頭揚棄於野蠻的過往,或歸諸於那些原始的『他者』。相反地,獵頭的歷史就存在於那裡,就在我的眼前」(p29)。這本書帶著我們睜開眼睛看看歷史、看看世界。
頭顱的故事
西元1599年出生的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是英國歷史中極具爭議性的人物。筆者實在很不熟悉英國歷史,所以沒打算對於克倫威爾先生臧否月旦一番。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2002年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舉辦的「最偉大的一百名歷史人物中」,克倫威爾先生名列第十;那麼,不論善惡,說他「總算是一號人物」應該還算公允。這樣一號人物死後被挖墳、車裂、戮屍。很驚悚嗎?驚悚獵奇的故事才剛開始揭開序幕。
他的頭顱被掛在英國赫赫有名的西敏寺。幾個幾世紀以來西敏寺一直是舉行加冕慶典、國葬及莊嚴演說的場所。頭顱高掛了多久呢?這本書上說四十年,維基百科說二十五年,筆者沒有能力查證,不過總之掛了幾十年應該總是有的。這顆望穿秋水且風吹日曬的頭顱直到被一場暴風吹落之後,展開了它坎坷的旅程。
從此,克倫威爾的頭顱輾轉流落在不同人的手中。一個來自瑞士的布商把它放在位於倫敦的私人經營博物館中,和異國花草與稀有硬幣一同展示。接著這顆頭顱淪落到了一個時常醉醺醺的演員薩謬爾(Samuel Russel)手中,在菜市場肉品區的攤位被當作娛樂買菜民眾的表演道具;後來它又輾轉成為不同人手中用以盈利的展覽品。
有購買力的鈔票會遭人偽造,能夠生財的頭顱當然也會有人假冒。換言之,關於這顆頭顱,幾百年來也上演過一些檢定真偽的戲碼。總之,一直要到二十世紀中,克倫威爾先生的頭顱才安息在劍橋大學的某處。
這本書的序幕就是從這裡開始展開的。書中的故事當然不止這一則;許多故事發生在最近一個世紀內,離我們一點都不遙遠,充分證明了前面提到的那句話「獵頭的歷史就存在於那裡,就在我的眼前。」
我們在繪畫或攝影中重現了頭顱,在藝術中感受衝擊、進行反思。比如說英國知名的藝術家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在1991年的時候發表了一張照片,內容是他本人咧著嘴微笑,和一旁面貌清晰的斷頭合照。上網搜尋「with dead head」 就可以看見這張照片。
你以為那只是某個瘋狂的藝術家個人的極端行為嗎?並不是。我們把人頭當成某種珍貴文物,在博物館裡展示。2007年時,謠傳英國牛津的皮特.裡佛斯博物館(Pitt Rivers Museum)考慮停止展示乾製首級,但是,「博物館的發言人表示,乾製首級是該館『頭號展品』,如果被撤下,小朋友會很傷心」(p69)。
在平和的非戰爭時期這些尚且理所當然,就更別說是戰爭時期了。我們把人頭當成戰利品,在戰場上斬下敵人首級用來炫耀/紀念。1944年五月美國《生活》雜誌的「每週照片」刊出一張照片:一位名叫娜塔莉的女人凝視著桌上由前線男友所寄來的禮物;娜塔麗一手拿著筆,一邊若有所思。而那個禮物,是一個日本軍人的骷顱頭;骷顱頭的血肉皮膚都已經刮除;這顆乾淨清潔的骷顱上還刻著十四名美國大兵的名字。
哦!天啊!我們人類那麼殘忍!難道不會受到神的譴責嗎?勸人為善的宗教不會對於這樣的行為加以阻止嗎?嗯,未必。我們在神龕裏保存了頭顱,在莊嚴肅穆的場合裡朝聖。比如說,奧立佛.普蘭基特(Oliver Plunkett)死於1681年;當他在1920年獲宣福時,他的頭顱已經擺在某個修道院超過200年。1975年獲封聖的他,成為七百年來愛爾蘭出現的第一位新聖人。「二次大戰以後,封聖運動工作人員用1.5便士的價格把碰觸過普蘭斯特頭顱和臉部的小布片賣給信徒,藉此收集活動所需資金」(p190)。又比如說,2011年,義大利的聖加大利納(Santa Caterina da Siena)封聖550週年的時候,世界各地的訪客不斷湧進聖多明我聖殿,拜觀她那包裹白紗的木乃伊頭顱(p194)。
充滿傳說的不止是這些封聖的頭顱;就算是犯人屍體,也充滿了神奇的力量。
如果你讀過魯迅的短篇小說《藥》。小說描述的是一個父親去刑場買血饅頭;因為他相信罹患肺癆的孩子吃了血饅頭就有機會痊癒。三十年前還是青少年的我天真的以為這樣的愚昧殘忍只是發生在特定國度裡特定時空下的悲劇,看了這本書赫然發現哎呀呀原來古今中外都一樣。「藥房裡通常也會存放一些人類骨頭或經過防腐處理過的遺骸,這些東西都被認為有助於恢復健康。人體的任何部位都派得上用場,......但人頭遺骨所含的力量特別強大。人類頭骨效用深遠,它被當成『一種特殊藥品』.....可以治療大多數頭部疾病」。在十六、十七世紀,不止藥劑師如此相信,醫生對於癲癇的處方簽,赫然也包括了一帖叫做「被斬首者的血」(p199)。直到1900年代初期,德國的藥學手冊及目錄還把木乃伊列為銷售商品之一,每公斤價格是十七馬克又五十芬尼(p202)。甚至於,來台灣開墾的漢人,直到日治時期,還會把「捕獲」的台灣原住民煮來吃,吃剩下的骨頭則熬製成藥膏,稱之為「蕃膏」。
既然說到犯人的屍體。我們把砍頭當成死亡儀式,在儀式中清楚照見人們/自己的瘋狂。別往遠處說,所謂的先進國家法國在1939年還有斷頭台的公開處決儀式。至於那一旁圍觀的群眾,打著哆嗦害怕的(天哪!那個人要被砍頭了!)、張大眼睛好奇的(哦!等一下他的頭要掉下來了)、亢奮不已高呼正義的(那種畜牲憑什麼被砍頭一死了之?應該先把他的手腳四肢砸爛再砍頭才對嘛!)......。一樣,都一樣。千百年來人性並沒有變化。
「唉呀,別這麼悲觀嘛!人性並不只是殘忍或愚蠢,也有科學理性的一面啊!」你可能會說。那就讓我們來看看,關於頭顱,歷史上的人類曾經多麼地「科學理性」。
「顱相學」在十九世紀的時候曾經是一門顯學。什麼是「顱相學」呢?它的立論基礎是這樣的:「一個人的性格可以透過研究他的頭顱來讀取。」十八世紀末的時候有個顱相學的大師,宣稱他辨識出二十七種人格特徵,並且宣稱這些特徵~~包括記憶、語言能力、狡猾、驕傲、機智、堅定等~~都位於腦部特定區域,而且具體烙印在頭蓋骨上(p218)。到了1860年,一位蘇格蘭顱相學家的著作《人體的構造》累積銷售量達到了十萬冊,一度超過達爾文《物種原始》的銷售成績。事實上,在1820年代初期,「法律系學生跟淑女們交際時,先聊拜倫的詩和蘇格蘭小說,然後告訴她們他非常相信顱相學」(p221)。大概就像我們今天把星座學當成一個必須參考的生活指南、一種值得研究的話題談資一樣。
這還算是光明面的了。至於人們為了要研究頭顱,曾經用怎樣的方式、搜集了多少頭顱、而這些頭顱又多數來自於怎樣的族群.....。這些歷史太黑暗了,筆者在此賣個關子,交由讀者自己來閱讀。可以確定的是:這樣子的搜集,即使到了「理論上人類已經文明許多了」的二十世紀,仍然以某種形式持續著。
人類基於各種你我難以想像的理由,而對頭顱動手動腳出了那麼多的花樣;在這麼多的花樣中,最能被你我所理解的,應該是基於醫學上的解剖--比如說醫學院的學生必須解剖大體。雖然那樣的場景在你我眼中看來實在不好受,但再怎麼想,醫學院學生練習解剖大體總是相當合情合理的一件事情。
即便如此,對於親手操刀的醫學院學生而言,心理上的壓力仍然是難以形容的;最可怕的是「有些東西看在局外人眼中是例行性的殘酷,但對圈內人而言卻只是例行公事」;就好像,「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下,人可以執行一些殘暴的程序,就像他們可以觀看血腥的處決,或將人頭煮熟以清除皮肉」。
總之,這本書帶著我們從各種場景看人類的頭顱~~從戰場、博物館、宗教聖殿、斷頭台、到醫院。繞了這麼一圈之後,最後提出了一個終極問題:頭被砍下來的那個剎那,斷頭者是有感覺的嗎?看起來是的;在那個剎那,那的人的「頭」仍代表「那個人」嗎?幾秒鐘後那個人顯然「死透了」,可是生命是在斷頭之後的哪個剎那、從哪個地方消失的呢?
今日醫學不斷突破昨日疆界,「換頭」技術已經不再只是科幻小說;早在1970年代,被醫生進行換頭手術的恆河猴已經可以存活數小時到幾天不等,而這還是三、四十年前的技術。人類的換頭技術成功之後,又會產生怎樣的倫理問題?
這樣的問題太深刻冷峻,已經超乎人類歷史的範疇,於是也只能提出一問之後,又付之一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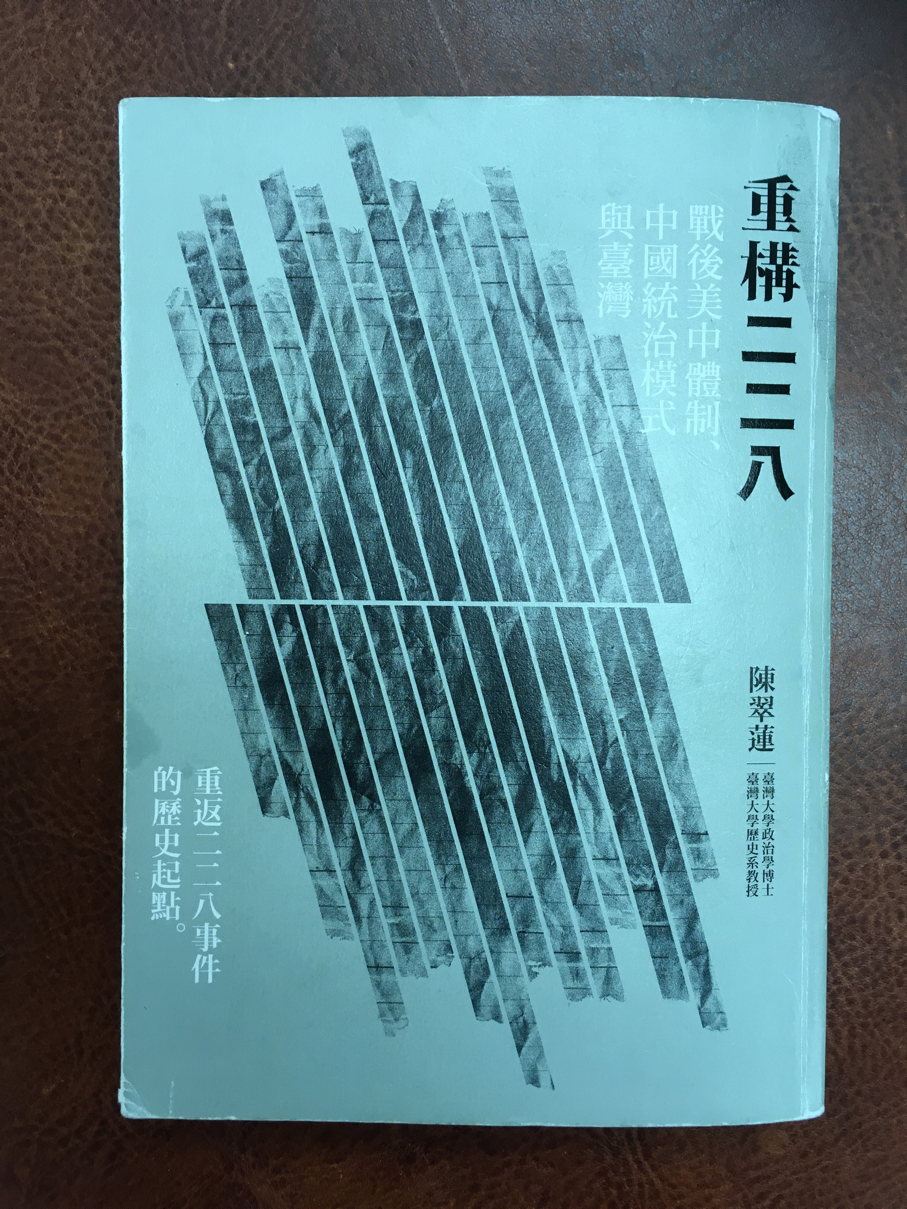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